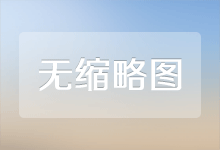原标题:沉重的底色与扭曲的方向——香港修例风波背后的一些社会深层根源
2019年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席卷香港。一个初衷是向台湾移交杀人犯的“修例”法案为何能引发如此巨大的动荡?
吹开喧嚣的政治泡沫,修例风波的背后有着一些香港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这些经济民生方面的矛盾成因复杂、长期未能解决,积累成巨大的社会问题。
很多青年眼中,未来缺乏亮色
都说青年人代表未来,但在很多香港青年眼中,未来缺乏亮色。
已满35岁的司机小邝酷爱摩托车,每到周末都会驾驶着大功率摩托车在郊野狂奔,这时候的他豪气勃发。但一谈起未来,情绪就低落下来。“未来,我们有未来吗?”没有房子,与家人挤住在一起,谈了多年的女友无法结婚,生儿育女的念头早已没有了。租房?30平方米房子月租金动辄八九千港元,小邝每月进项不过1.5万港元左右,如何能租?至于攒首付买房,更是想也不要想。你攒钱的速度绝对比不过房价上涨的速度。
对比一下香港房价上涨幅度和收入上涨幅度,可以看得很清楚:目前,香港不同区域、房型价格不等,但绝大多数都在每平方米20万港元以上。而月收入呢?一位市民向记者表示:“20年前,大学毕业生就拿一万港元了,20年过去,涨到一万二、一万三,这20年,物价涨了多少?算上通胀,大学毕业生实际是贬值的。”
按国际劳工组织2018年的数据,从2008年到2017年,内地的实质薪资成长率达8.2%、澳门1.6%、韩国1.2%,台湾的实质薪资成长仅0.2%,香港甚至落后于台湾,只有0.1%。而从2004年至2018年,香港房价涨了4.4倍。
正是房价高涨、薪金收入停滞,导致香港自有住房比例下降,从2003年至今,香港的住房自有率从53%下降到48.9%。这个数据的背后,是财富更加集中,是多少青年自有住房梦破灭。
像小邝一样,假如只活在当下,不考虑房子,吃喝、逛街、郊游倒也不愁,只是“千万不要去想未来”。
中产的“坠落”焦虑
中产阶层一向被认为是中坚力量,是社会的稳定器。但在香港,这个稳定器正在失灵,担忧向下坠落的“中产焦虑”在香港尤为突出。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前局长张炳良对此有个概括叫“中产阶层的基层化”,何意?“就是说,这个阶层的教育水平、文化认同是中产,但实际生活已经达不到中产阶层的水平,与基层趋同”。
在香港,2018年月薪中位数为1.75万港元,公务员和教师中位数2.84万港元,论整体收入已经相当高。但张炳良透露,他做局长时做过公务员住房的小调查,惊讶地发现,不少人买不了房子,有的甚至住在劏房(指一个住房单位被切割成多个很小的居住空间)中。
就香港而言,房产,是富人的财富,是中产昂贵的门票。没有退路的香港中产,为了获得这张门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括极高的负债、透支性的消费以及束缚性的职业生涯。所谓香港中产,就像在房子这个通道里的沙子,随着房价波动,在有产和无产两端之间来回颠倒。
持续增长的高房价,将香港社会撕裂成有房者与无房者两大对立面。没“上车”(拥有住房)的想“上车”,“上车”的立刻变成高房价的维护者。正是各种不同利益主体的复杂纠葛,让香港特区政府左右为难,动辄得咎。近来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为应对土地供应不足而推出的东大屿山填海计划,作为一计解决房屋问题的长远方略,却遭到了很多人的无端质疑。
上升通道狭窄,“哑铃型”社会成型
作为一个高度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社会,香港仍有数量不少的穷人。香港社会贫富差距大、阶层固化的背后,是产业的高度单一和空心化。
根据统计,2016年,香港显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539,已大大超过危险警戒线的0.4,与部分拉美国家持平。尽管特区政府为解决贫富差距做出了不少努力,但社会福利水平与香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很不相称。
在健康的社会里,青年和基层人士通常可以通过就业、教育等途径实现向上流动。但香港的社会阶层却基本固化,例如,位居富豪榜前列的人士多年未曾变化,基本都是地产商及其家族。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而产业空心化是青年上升通道日渐狭窄的主因之一。
在20世纪70年代香港有将近一半的劳动者是产业工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香港金融、航运、商贸物流、服务业兴起,管理、行政、技术、金融及专业人才吸纳众多劳动力,跨入中产阶层。但在随后的产业升级中,在原有商贸、航运之外,只发展了金融、旅游等服务业。
“科创产业没能发展起来是香港的一大痛点,”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荣休教授雷鼎鸣说,“香港金融业占到了GDP的约19%,但只提供约6%的就业。”金融业创造财富的能力惊人,但只能吸收少数本土精英青年人,大部分本地青年没有能力从事高端服务业,何况许多香港金融从业者更是来自海外的人才。
对于当前的局面,特区政府曾尝试采取多种手段予以改变,但科技创新产业几次努力,几次夭折。这其中,反对派曾出于政治目的进行过种种无端阻挠,比如特区政府为推动创新科技发展而成立的创科局,反对派为反而反,不顾社会一再呼吁停止政治虚耗的呼声,在立法会百般阻挠,生生拖了三年。
这直接导致香港制造业产值时至今日仅占香港GDP的1%左右,吸纳劳动力寥寥无几。
政治争拗持续,难题更难消解
高房价、贫富差距、青年难以向上流动。这些社会问题早已暴露,回归22年来,历届特区政府也都做出过不同程度的努力。但迄今为止,收效甚微,民怨难以消解。这是修例风波一经煽动就爆发的重要原因。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田飞龙说:“回归以来,由于多种原因,特区政府确实没能更多地通过政策保障、民生保障合理地去解决香港的社会民生问题,导致香港有很强的内生动力将经济民生议题政治化。”
不可否认,有些民怨确实是特区政府政策上缺乏远见所导致的。但香港深层次矛盾之所以难以化解,既有政治架构上的互相牵制,造成施政困难;也有政府举措失当,还有长期以来自由市场理念下,教条式执行“小政府、大市场”的理念带来不作为的问题,而最主要的是,反对派不断制造和挑起政治争拗,罔顾经济民生大局,人为制造了各种困难。
这些因素盘根错节,再加上各种利益集团各求所好,别有用心者趁机搅局,结果问题不断在讨论,措施迟迟不能出台,时间流逝,矛盾积重难返。
典型莫过于提高房屋供应量。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提出了每年增加8.5万套住房的计划,但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房价大跌,计划只能取消。